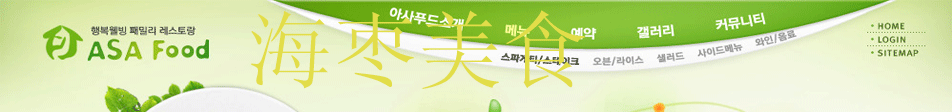|
庆祝赵宋光先生85岁华诞特辑 在赵宋光先生迎来85岁华诞之际,本平台推出专题特辑,向为草原音乐的研究、编创以及人才培养做出杰出贡献的赵宋光——沃根奥其先生,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愿! 感怀 ——祝贺赵宋光老师85岁华诞 宋光吾师,沃根奥奇。乐坛泰斗,有口皆碑。品德高洁,淡泊名利。为人谦和,作风平易。生活简朴,远离奢靡。粗茶淡饭,温饱足矣。宋光吾师,献身教育。辛勤耕耘,桃李满地。为人师表,解惑释疑。有问必答,耐心仔细。宋光吾师,才华横溢,知识渊博,学贯中西。多项学科,开僻奠基。精研美学,探究吕律。五声调式,自成体系。宋光吾师,深明大义。民族团结,践行不移。蒙古音乐,追求不止。草原情结,始终如一。九九明珠,哲理启示。向往内蒙,第二故里。宋光吾师,一身正气。文化自信,坚持真理,崇洋媚外,向来鄙弃。大家宋光,傲然特立。大师宋光,无可企及。 ——85华诞,恭贺致礼。吾师长寿,百岁可期。学生幸甚,可循可依。乌兰杰上,谨表敬意。特此。 年11月6日于北京 《赵宋光先生的“草原情结”》(上) 作者 乌兰杰 追求篇 不寻常的“冬之旅” 赵宋光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性格特征,包括他的学术活动在内,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:追求,创造,奉献。作为他早年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学生,我是从一个蒙古人的眼光来观察他,认识他,解读他,并得出这个结论的。赵宋光先生对蒙古音乐的酷爱,对草原文化的追求,并实现其心灵和精神上的皈依,算来已有48年之久了。这比起他的学术活动来,时间上要早得多。我想,他之所以走上一条“赵宋光式”的学术道路,恐怕与内蒙古地区的特殊因缘,以及蒙古音乐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。 我初次见到赵宋光先生,是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,时间是年的2月份。当时,赵先生还是一名年方21岁的大学生,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。我那年才14岁,胸前飘着红领巾。我的姐姐斯琴塔日哈是内蒙古歌舞团的舞蹈演员,她把我从偏远的老家接出来读书。 塞北的严冬寒风凛冽,大雪飞舞,万物凋零,作为一介南国学子,赵宋光选择这样的季节游历内蒙古,委实令人有些感到意外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随同他的两位蒙古族同学——美利其格和包玉山来到呼和浩特,作此次不寻常的塞北“冬之旅”的。美利其格是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一歌的作者,蒙古族著名老一辈作曲家。包玉山则是蒙古族第一批接受新音乐教育的人,内蒙古歌舞团首任乐队队长兼指挥。年秋,他们两人同时考入中央音乐学院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音乐学院大学生。 美利其格和包玉山,既是求学深造的大学生,又是特殊的蒙古族文化使者。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许多师生,对内蒙古地区和蒙古族情况知之甚少,就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内蒙古和蒙古族,乃至蒙古音乐的。对此,辛沪光女士后来回忆道:“我于年夏天报考中央音乐学院,校方腾出两间大教室,搭起通铺,分别安排男女考生住宿。不久,从男生宿舍里传来悠扬的马头琴声,引起了人们的好奇。有些人跑过去打探,原来是来了两个蒙古族考生,其中一位会拉马头琴。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汉族学生,从来没有见过蒙古人,更不知马头琴为何物。于是,都跑过去看望那两位蒙古族同学。会拉马头琴的叫美利其格,后来竟是我的同班同学。”至于考入管弦系的包玉山,辛沪光通过向他了解和学习蒙古族音乐,不仅建立了友谊,并且产生了爱情,最终结为伉俪。 赵宋光认识和接触两位蒙古族同学,则远没有辛沪光那样富有戏剧性,带有罗曼蒂克色彩。然而,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时期认识美利其格和包玉山,并跟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,堪称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件大事。赵宋光——这位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学过来的学生,思维敏捷,感情细腻,具有超凡的洞察力。他从两位蒙古族同学身上所发现的,不仅是他们魁梧健壮的体魄,热情开朗的性格,骑马挎枪走天下的革命文艺战士生涯,以及参加过辽沈战役的传奇经历……;更令赵宋光感到新奇而且着迷的,是美利其格和包玉山所唱的蒙古民歌,以及向他随意讲述的蒙古社会风情,古老的民间传说等。 年8月,安波、许植、胡尔查所编译的《东蒙民歌集》出版了,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行的第一部少数民族民歌集,赵宋光是早就研读过了的。然而,当听到蒙古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演唱民歌——包括他从《东蒙民歌集》上已经学到的民歌时,才发现那些载入歌集的民歌曲谱,并没有能传达出民歌“活”的灵魂。他终于悟出这样一个道理:从书本上学习民歌固然重要,但却永远不能替代从生活中学习民歌。于是,赵宋光便暗暗定下决心:随同美利其格和包玉山到内蒙古草原去,亲自到产生蒙古民歌的地方去听、去学蒙古民歌! 年寒假,赵宋光随同美利其格北上,来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。在美利其格和包玉山的安排下,他日夜忙碌,如饥似渴地学习蒙古民间音乐。拜访了几位著名的民间艺人,如“潮尔”(古老的马头琴)演奏家色拉西、说书艺人毛依罕、盲艺人铁钢,以及长调歌唱家哈扎布、宝音德力格尔等人。他全身心地聆听这些民间艺术家的演唱、演奏,真正接触到了蒙古民间音乐的精华,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 宝音德力格尔是一位来自呼伦贝尔的女歌手,年方21岁。她原是草原上的牧羊姑娘,淳朴善良,性格爽朗,聪明伶俐,具有超凡的音乐天赋,且天生一副好嗓子,擅长家乡的长调民歌。诸如,《辽阔的草原》、《褐色的雄鹰》、《巴颜巴儿虎的马群》等民歌,都是由她首唱并推广开来的。宝音德力格尔的歌声,充满着无限魅力,赵宋光被深深地迷住了!为了能和宝音德力格尔自由交谈,进一步学习蒙古民歌,他竟开始学起蒙语来…… 一首蒙古民歌中这样唱道:“天上的大雁从南往北飞,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。”赵宋光在隆冬季节造访内蒙古歌舞团,目的就是为了追求——追求自己所喜爱的蒙古族民间音乐。这便是此次不寻常的“冬之旅”背后的简单原由。 赵宋光先生与李兴武教授、长调大师宝音德力格尔、歌唱家木兰等人一同 “斯琴塔日哈的弟弟” 我进入赵宋光先生的视野,乃至闯入他的生活,可以说是比较早的。 我小时候生长在科尔沁草原,熟悉民间音乐,会唱许多蒙古民歌,又会模仿胡尔奇说书,因而很受内蒙古歌舞团大哥哥、大姐姐们的喜爱,被亲切地称之为“斯琴塔日哈的弟弟”。寒假中的一天,姐姐告诉我说:“中央音乐学院来了一个叫赵宋光的人,想听你唱民歌。”于是,我被领到他下榻的房间,见到了赵宋光。我当时很高兴,一口气给他唱了好几首家乡的民歌,还表演了一段说书。赵先生全神贯注地听着,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。我唱过歌后,他夸奖我唱得好,并且要求我再讲一段民间故事,于是我又讲述了一段民间故事给他听。时至今日,我已回忆不起当时究竟唱了些什么民歌,讲述了哪一则民间故事;唯独赵先生张着大大的眼睛直视我的形象,深深印入我的脑海,依旧那样鲜明,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。 年秋天,即认识赵先生之后不到半年,我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“少年班”——音院附中的前身。我和赵先生在校园里重逢,感到十分高兴。从此,我们经常见面,彼此接触自然也就多了起来。年秋,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,考取了本科音乐学系。凑巧的是,赵宋光先生当时已是该系教员,我们遂建立起师生关系。 年春,中国音乐学院成立,我们这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学生,都来到了“大观园”,赵先生依旧是我的老师。一年后,我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并留校工作。自此,我们又成了同事。然而,无论从年龄、资历、学识方面来说,赵宋光先生仍旧是我的老师,这是没什么可说的。 赵宋光先生与乌兰杰先生 草原——黄河 年,岁在壬申。赵宋光先生人生道路上的许多重大事件,恰恰都集中发生在这一年。如前所述,他与内蒙古文艺界建立联系,已有3年多了。在此期间,他以自己的真诚和勤奋,一件又一件实际行动,感动了蒙古族同胞,以及内蒙古歌舞团的许多朋友,取得了他们的信任。蒙古谚语云:“命运的神马飞驰而来,惟有准备好了的骑手才能抓住缰绳。”是的,赵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整装待发的骑手,牢牢抓住了疾驰而来的神马之缰。 年夏,内蒙古歌舞团著名舞蹈家贾作光,准备创作一部蒙古民间题材的独幕舞剧,为翌年的自治区成立10周年献礼。他特意邀请赵宋光先生为该剧写音乐,赵宋光则痛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。为了搞好舞剧创作,两位作者约定到草原上去体验生活。赵先生赶到呼和浩特与贾作光会合,坐上人货同载的大卡车,一路颠簸地赶往锡林浩特,准备深入到草原牧区去。作为一个在大城市中长大的内地人,赵先生首次在草原上长途旅行,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呵。他这样写道:“我第一次领略到草原的辽阔,前面的山梁看着好象不远,车越驶近,反倒越觉得它远了。草原上没有路,车辙重复得多了,就成了一条路。有时,为了免于陷进泡烂了的沙道,车要朝着没有路的草地开过去。这样的体会,在我都是第一次。它们默默地向我诉说:草原的主人并不在乎有没有路,路近路远,投向无垠的辽阔,就是生命的酣畅。”⑴ 草原城市锡林浩特,是锡林郭勒盟公署所在地。赵宋光先生在那里受到热情接待,并且欣赏到了盟歌舞团的蒙古舞蹈表演,长调民歌演唱,以及马头琴、四胡、笛子演奏;认识了当地的几名蒙古族艺术家。遗憾的是,贾作光临时有事进北京,他们没有能按计划深入草原牧区去,只好返回呼和浩特。此时,内蒙古歌舞团已离开呼和浩特,奔赴宁夏银川演出,准备从银川再到内蒙古西部的巴音浩特。本来,情况已经发生变化,赵宋光可以名正言顺地返回中央音乐学院。但他却没有那样做,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追赶内蒙古歌舞团的演出队,到巴音浩特去! 黄河百害,惟富一套。 从呼和浩特到银川,火车只通到包头。自包头至磴口则是一段土路,只能乘坐人货同载的敞篷卡车。从磴口西渡黄河,便可进入宁夏境内,径直前往银川。赵宋光果真来到磴口渡口,独自站在黄河岸边。面对着无语东流的黄水,他心潮澎湃,千言万语,汇成一句内心的独白:“多久一直想见的黄河,这回总算见到了。”⑵乘船摆渡时,他听到船工发出粗重的吆喝声,看见被世代蹬踏而深深凹陷的岩石,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。 当赵宋光突然出现在银川招待所时,内蒙古歌舞团的朋友们无不惊讶。诚如他自己所说:“我来到此地,一无向导,二无伴侣,三无商量,四无约定。是谁把我引来了?是草原的博大,是黄河的激荡。就象一路上的那些沙丘,我在期待河水的浸润……”⑶在银川的那几天,他每晚欣赏蒙古族的歌舞器乐演出。对赵宋光说来,内蒙古歌舞团的精彩节目,是浓缩在舞台上的草原风光,犹如醇厚的美酒,飘香的奶茶,使他深深陶醉。 赵先生随同内蒙古歌舞团一行,翻越贺兰山脉来到巴音浩特。是年,阿拉善、额济纳二旗刚划归内蒙古,正举行盛大的那达慕,以及一系列庆典活动。那达慕,蒙语意为“游艺”,是蒙古族特有的传统节日。届时,草原牧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,举行“男子三项竞技”——赛马、摔跤、射箭,开展群众性歌咏比赛活动,形成独具特色的草原民间艺术狂欢节。那达慕又是热闹的草原集市,蒙古人趁机销售和购买各种商品,展示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、饮食、精美的工艺文化。总之,那达慕是草原生活的橱窗,集中体现着蒙古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如果不参加那达慕大会,便不可能生动、直观、全面地了解蒙古族的草原文化。 赵先生有幸参加此次那达慕,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他写道:“我住进了那达慕大会会场的蒙古包,又第一次看见了摔跤、赛马、骑着马的射箭砍桩比赛。最难忘的是彻夜不停的歌声。在我们住的蒙古包里,请了几位牧民来唱,我来记谱,歌舞团的词作家记歌词,工作到深夜,大家就休息了。这时,周围的蒙古包里还在唱着。五更醒来,远处仍传来悠扬的歌声,在晴朗的夜空下回荡,回荡。蒙古族的普通牧民热爱音乐到了什么样的程度……”⑷ 内蒙古歌舞团取道银川,准备返回呼和浩特,但赵先生却提出:要走水路!宁夏银川至内蒙古包头一段,黄河水道可以通航,但却只有货船而无载人的客船。此时的赵宋光犹如久别母亲的游子,心中产生了亲近黄河,拥抱黄河的强烈愿望。于是,他从横城码头登上一艘运米船,浩浩汤汤,向东北方向泛舟而去。“黄河九曲十八弯”,一路饱览两岸风光,体味到水上航行的种种乐趣,堪称心旷神怡,其乐无穷。 赵先生的此次“黄河之旅”,犹如一首交响诗,波澜壮阔,扣人心弦。一路上的所见所闻,使他终生难忘。他写道:“艄公告诉我,前些日子有一条船撞在岩石上,翻了,沉底了。……大家坐稳,谁也不走动,谁也不说话,绷紧心弦,一片寂静。我体验到了‘生命系于技术’的边缘状况。虽然共计不过半小时,它却成了我一生永久的记忆,不停地教导我以高度责任感对待技术细节。”⑸ 当船工们与黄水搏斗的时候,赵宋光听到了船工号子。木船行进中有时难免搁浅,此时人们便“脱下衣裤跳进河床,肩并肩,用背部扛起船底,把船掀起来,顶出去。每逢这样的场合,领头的船工都要吆喝号子:‘哎——哟——兄弟们!……’号子的音调通常以商音上的长音开始,上下流转之后,在宫音上站住。我明确地感到,当音调下行时,宫音总要偏高一些,从中,我获得了‘四分之三音’这音程概念。”⑹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,往往是由几次大的选择构成的。赵宋光先生的第二次草原之行、黄河之旅,堪称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次最为重要的选择。难怪,他后来发出这样的慨叹:“命运赐的机缘。多年以后我才懂得,那是独一无二不可再得的。”⑺确实如此。亲临广阔草原,聆听蒙古牧民唱民歌,使他真正感受到“草原文化”的博大精深。航行黄河水道,聆听船夫唱《黄河船工号子》、《爬山调》,则使他切实体味到黄土高原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厚底蕴。自那时起,黄河伴随着时光整整流逝了45年。然而,赵先生内心深处的“草原——黄河”情结,却不曾有丝毫变化。它们如同车之两轮,鸟之双翼,推动着他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。黄河烛照生命,草原净化心灵,几十年的实践证明,他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,奉献给了黄河和草原。 赵宋光先生在内蒙古采风 赵宋光先生与吕宏久教授、李兴武教授等一同 漫游乌兰察布草原 年秋,唐山大地震后不久,一位蒙古族朋友敖其尔从呼和浩特来北京。我们劫后重逢,感到分外高兴,便相约一起聚会小酌。我知道赵宋光先生素来关心内蒙古,便特邀他参加此次聚会。我们饮酒唱歌,谈笑甚欢。敖其尔则十分钦佩赵宋光先生,他提出一个建议:赵老师如此热爱蒙古民族,喜欢蒙古音乐,应该说是蒙古族的忠实朋友。按照我们的民族习俗,应该有一个响亮的蒙古名字。我对他的建议拍案叫好,赵宋光先生也赞成此议。那么,究竟给赵老师起个什么样的蒙古名字呢?我记得他有一个笔名叫做“方耀”,大凡发表人类学、哲学方面的文章,他都喜欢签署这个名字。我觉得“方耀”二字立意甚好,遂同敖其尔商议,用蒙语将“方耀”译为“沃根奥奇”。赵宋光先对“沃根奥奇”这个蒙古名字十分满意,表示愿意采用之。从此,他便有了一个响亮的蒙古名字——沃根奥奇。 年5月,我离别了生活和工作近20年的北京,调到呼和浩特,在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工作。从此,我和赵宋光先生身处两地,接触自然少多了。6月下旬,我们分手才一个多月,他便来到了呼和浩特。我们商定:赴乌兰察布草原,游历达茂联合旗,领略蒙古族牧民的生活风情,实地考察那里的民歌。赵先生初游草原是年秋,距今已有21年之久,我自己阔别草原也有十几年了。我们共同的心愿是,再次投入草原的怀抱,回归大自然,让和熙的塞外风带着青草野花的芬芳,洗涤“十年动乱”中内心沉积的尘埃。 我们之所以选择达茂联合旗,还有一层原因:我有一位亲戚陈天亮是那里国营红旗牧场的场长。他负责安排我们的此次旅行,并且答应把自己的吉普车让给我们专用。此次旅行格外顺利,收获良多,与他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。 我们在达茂联合旗的主要日程,自然是收集蒙古民歌。正值草原大忙季节,牧民终日在野外繁忙劳动。由于陈天亮场长为我们提供了吉普车,采访牧业点十分方便。何况,蒙古族司机昌纳,性格爽朗,酷爱民歌,本人就是很不错的歌手。他对当地的民间歌手了如指掌,遂成为我们的义务向导。 巴德玛,是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年妇女,当地有名的民歌手,我们第一个采访了她。巴德玛为我们演唱了几首风格纯正的乌兰察布民歌。诸如《金色圣山》、《细长的黄骠马》、《雪山》等。赵宋光先生听着巴德玛的歌声,为之动容,唏嘘不已,一再夸奖她唱得好。巴德玛是一位极富音乐天赋的人,嗓音清亮,气息通畅,艺术表现力强。她与我们两人交谈,落落大方,充满自信,几乎看不出是一个盲人。显然,她从歌声中找到了快乐,体味到了自身的价值。 韩德操,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女歌手,名声不如巴德玛大。她为我们演唱了《圆圆的树冠》、《十二属相》等民歌,歌声深沉苍凉而多情。据说,她从小多病多灾,父母许愿将她送入佛门,落发当了尼姑。不料她后来竟出落成一名美女,且歌儿唱得又好,使当地年轻人惋惜不已。年,当地寺庙合并,韩德操还俗回家。不久,父母兄弟相继去世,留下她独自一人。当地人认为韩德操“命相”硬,克死了全家人云云。人言可畏,从此,人们不敢接近她,更不要说向她提亲了。韩德操有不少自留畜牛羊,家境殷实,却没人为她帮工放牧。年,一位汉族农民逃荒至此,为蒙古族牧民打工糊口。他十分同情韩德操,经常抽空帮她干些重活。韩德操平日也多方照顾这个无家无业的光棍汉。两个不幸的人,竟超脱民族的界限,逐渐产生了纯真的爱情。我们采访韩德操时,他们俩已经一起过日子了。 昌纳,他所掌握的民歌并不多,但却有一个特殊本领:擅长即兴编词,随口就能唱出一支“新民歌”。陈场长为我们接风的宴会上,他自告奋勇地编唱了欢迎我们的新民歌。我们每逢采访一处新牧业点,他都留心倾听歌手演唱,学习自己所不知道的民歌。此次采访时间不长,但却收获不小,与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。 我和赵宋光先生回到呼和浩特,陈天亮场长的女婿陶特毕力格(我的本家弟弟),专门设宴为我们接风。满都夫和那仁巴图两位朋友,应邀前来作陪。满都夫是赵宋光和我在中国音乐学院时的学生,那仁巴图是内蒙古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员。我和那仁巴图是业余歌手,经常应邀参加呼和浩特蒙古人的宴会,联手为大家演唱民歌。这次纯粹蒙古式的宴会上,我和那仁巴图通宵达旦为赵先生唱了许多民歌。赵宋光先生异常兴奋,也多少有些惊讶:大城市里生活的蒙古人,竟如此完整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风俗,熟悉和热爱自己的民间音乐,这是他始料不及的。 赵宋光先生采访鄂尔多斯民间歌手扎木苏先生 创造篇 钢琴变奏曲: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 赵宋光先生的创作活动,是从作曲开始的。他转向音乐理论,那是后来的事情。 年深秋,内蒙古歌舞团赴天津演出,专程访问了中央音乐学院,并与该院师生进行联欢。在此次联欢会上,赵宋光登台演奏了他的新作——钢琴变奏曲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。该曲创作于年底,是他的毕业作品,主题采用了美利其格的同名歌曲音调。在这部大型独奏曲中,作者怀着一颗赤诚的心,着力表现蒙古族同胞翻身解放的欢乐,以及草原儿女热爱和平,热爱家乡,用勤劳的双手建设新生活的豪情。赵宋光的演奏热情洋溢,技巧娴熟,受到内蒙古客人和音乐学院师生的一致好评,获得很大成功。 青年时代的赵宋光,弹得一手好钢琴,当时算得上是一位很不错的钢琴演奏家。因此,他写钢琴曲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堪称得心应手,充分发挥出钢琴的表现性能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对于我国作曲家而言,如何运用西洋乐器来表现新生活,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新生活,音乐创作上体现民族化,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。赵宋光创作这首乐曲时,为了表现新的内容,在作曲技法方面作了很多探索。尤其在和声语言方面,更是花费了大量心血,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。 钢琴变奏曲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的产生,并不是偶然的。它是作者热爱蒙古民族,向往辽阔草原的真情流露,集中展示了自呼和浩特“冬之旅”始,努力学习蒙古音乐,追求草原风格所取得的成果。 著书立说,创立体系 年8月,赵宋光先生从巴音浩特回到了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。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,改变了赵宋光的舞剧音乐创作计划,乃至他的人生历程。 随着新中国广播事业的迅猛发展,国家急需一批高级广播技术人才,决定派人到东德留学,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培养音响导演、高级录音师。当时,国家要求中央音乐学院推荐一名学生。校方经多方面考虑,最终选中了赵宋光。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,国家需要高于一切,服从组织安排是天经地义的事,赵宋光自然也不例外。他得到校方通知后,立刻从内蒙古赶回中央音乐学院,办理出国留学手续。当时,他正在和指挥系女同学、转业军人史介绵谈恋爱,出国留学打乱了他们的计划,于是决定提前结婚。年10月10日,赵宋光告别了新婚妻子,踏上了出国留学的路程,入东德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学习。 赵宋光先生对我谈起过留学德国时的一些情况,至今记忆犹新:中国留学生抵达东德后,为了摸清他们的学业程度,高等音乐学校方面安排了一次入学考试。赵宋光先生在考场上演奏了他的毕业作品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变奏曲。德方主考官对他的演奏非常满意,也多少有些惊讶,没有想到中国竟会派遣这样高水平的钢琴家来学习音响学。 他们在东德上课,德语翻译不懂音乐,感到非常吃力,长此以往,必将影响学习。于是,赵宋光挤出时间强攻德语,三个月过后,便主动请缨担任翻译,并圆满完成了此项工作。 东德方面派来一位年岁较大的女士,担任中国留学生班的生活管理员。此人责任心极强。但却严格得近乎刻板,像管教小学生一样地管理他们。她尤其不准留学生随便上街,以防发生意外。这倒为赵宋光节省了不少时间和金钱。他买来许多新书一本又一本地阅读,既打发课余时间,又增长了许多知识。 赵宋光先生从东德留学归来后,并没有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工作,而是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。有一天,赵先生把我请到家里,郑重其事地告诉我:他正在写一部有关五声音阶调式方面的书。该书第七章“七声音阶”部分,缺少“徵羽调式”的例子,希望我能向他提供一首这样的蒙古民歌。当时,我学的是苏联斯波索宾的《和声学》,从未听说过什么“徵羽调式”。于是,他向我扼要地介绍了“五度相生调式体系”的要点,以及“徵羽调式”的特征。经过一番回忆,我终于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民歌中,选了一首婚礼歌《太阳里的松树》唱给他听。 赵宋光先生聚精会神地听着,他的那副神情,不禁令我回想起在呼和浩特唱民歌时的情景。他对《太阳里的松树》非常满意,赞扬备至,认为是一首难得的好歌,完全符合他的要求。后来,他果真将此歌作为“徵羽调式”的唯一谱例,引用在他的书里。他写道:“这是一首很出色的民歌。把羽调浓色彩音用到徵调式里来,给这曲调带来了鲜艳的色彩变化,使它富于活力。这个附加音的表情作用是很突出的,传达出做母亲的对亲女儿的温存和送别时的深沉情感。”⑻在该页的注释中,他特意写道:“这是扎赉特旗的一支送嫁歌,是蒙古族的扎木苏同志唱给我听的。”扎木苏——这个普通蒙古族大学生的名字,堂而皇之地上了“本本”,这还是第一次。诚然,赵宋光先生在并不掌握实例的情况下,断定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中应该存在“徵羽调式”,是基于理论上的科学推断。至于他认定“蒙古族同志”扎木苏应该知道这样的民歌,则远不是中央音乐学院一般教员所能做到的。只有了解内蒙古文艺界情况,深入研究过蒙古民间音乐的人,才能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。 年8月,赵宋光先生的《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》一书出版了。 |